3月12日植树节到了,人们在对近日持续的雾霾原因不停发问时,也把目光投向北京的树木与绿化。
如今,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高大的建筑正代替一片片树林,宽阔的柏油马路正覆盖一块块绿地,零星散布的行道树无法遮挡酷热的烈日,鸟语花香也只能到公园里去寻觅。
而这一切景象都像电影一样,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到来。就像秋天带走枯叶,流逝的岁月也改变着北京的树种。
乡土树种在城市中比例减少
说到北京的树种变迁,首先要界定一个时间范围,十年、百年,还是千年?只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长度,才可以更准确地度量树种变化的蛛丝马迹。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翔看来,从沧海桑田这种地质运动的跨度来解析北京树种的变迁显然过于宏观了,北京的树种变迁更多集中在近100年来。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随着北京城市格局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北京的树种在变与不变间艰难演变。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全儒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对北京乡土树种现状进行了调查。共调查了北京市区22处公园绿地、8处广场绿地、10处学校绿地、20处小区绿地、50处道路绿地,其中常用乔木约40种,主要有油松、侧柏、圆柏、白皮松、国槐、毛白杨、银杏、洋白蜡、旱柳、法国梧桐、合欢、香椿、栾树和臭椿等。
调查发现,乡土树种在城市绿化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100多年来,我国城市园林绿化大量从海外引进外来树种,如法国梧桐、洋槐、加拿大杨、洋白蜡,使城市生态失去了原有的特色。
跨越百年的“皇家树种”
在100多年前,溥仪还没有退位,北京城还是紫禁城、内城、外城的格局。紫禁城就是今天的故宫,皇帝住在里面;内城就是今天地铁2号线这一圈圈起来的地方,住着大小官员和商人;外城就是南边儿凸出来的那圈儿,从东到西分别是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西便门,这里住着普通老百姓和一些手工艺匠人;城外是郊区,基本是菜地。
那时,城里与城外的树种是不同的,而紫禁城与内城、外城的树种也不相同。张志翔告诉记者,100多年前,在紫禁城和一些皇家仪式场所种植着大量“皇家树种”(这里暂且用皇家树种的概念,是由于这些树在故宫、天坛等地现存大量古树)。如今,在故宫、天坛公园、地坛公园、月坛公园中都保存着很多“皇家树种”,比如侧柏、圆柏等,由于这些树种不畏寒暑、四季常青、寿命长,在古人看来具有长寿的象征,种植在皇帝生活、居住、办公以及社交的地方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在北京的皇家园林中多有种植。
记者在天坛公园中就看到许多百年以上的侧柏,尤其在祈年殿南面皇帝祭天的步道两旁,尽管有些侧柏有雷火烧击的痕迹和被虫子掏空的树洞,但仍然参天屹立、郁郁葱葱,衬托出皇家园林的庄严肃穆。
而侧柏、圆柏还被人们赋予坚强、独立、坚贞的形象,清代诗人曹一士曾在《咏古柏》中写道:“桃李艳春日,松柏黯无光。贞心结千古,誓不随众芳。”这种特质也让侧柏和圆柏成为北京保持至今的主要树种之一。
与建筑共存亡的寺庙树种
历史上,北京城内城外有许多寺庙、道观,前面提到的侧柏在寺庙中也大量种植,除此之外,还有油松、银杏、白皮松、楸树等。
张志翔告诉记者,当年,楸树曾在寺庙中大量种植。传说汉武帝出巡时曾在一棵大树下乘凉,顿感凉风习习,周身凉爽,于是问旁边的农夫:“此为何树?”农夫答:“是楸树。”
楸树容易栽培,而且可以笔直生长到二十多米高,顶部形成一柄大绿伞,遮阴效果好。而且楸树成材率高,花纹优美,质地坚硬,不变异,耐磨损,抗虫蛀,是做家具的好材料。
由于楸树材质好,耐腐蚀,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中棺木的优质用材,一般爷爷在孙子降生时,即栽上几棵楸树,待孙子长大娶亲时,伐树建房或做家具,同时,也可用于老人的棺木。但也正是因为楸树生长期太长,导致后来被慢慢淘汰了。著名作家刘心武在他自传中就曾经回忆北京隆福寺大殿旁有一棵大楸树,而如今已随大殿一起消失了。在张志翔印象中,故宫后花园里还保留着一株大楸树,大觉寺等还存有古老的楸树。
在北京寺庙中另一种种植较多的树种是银杏树,银杏是最长寿的树种之一,有“寿星树”之称,银杏树体高大雄伟,最能衬托大雄宝殿的壮观。其叶片洁净素雅,有不受凡尘干扰的宗教意境,因此,有人称银杏为“中国的菩提树”,而且它们大多是一雌一雄种植在寺庙的大殿前,如北京的潭柘寺就是典型的代表。后道家也视银杏为祥瑞之树,在道观中也有种植。
尽管经过历史变迁,许多北京城内的寺庙和道观已经消失,但保存下来的寺庙、道观中,这些银杏树也一直保留下来。而且现在,在一些公园和街道两旁银杏树也作为绿化和行道树种植。如天坛公园东门附近、高碑店的兴隆公园里,以及三里河路两侧。
可以说,大部分北京寺庙树种的保存与消失和寺庙、道观建筑的存亡有关,保存完好的寺庙、道观里,这些树种都健康生长。
消失的市井树种
与大部分保存完好的皇家树种、寺庙树种相比,北京的市井树种则有较大变化。
在张志翔看来,说到北京的市井树种,不能不提胡同中的乡土树种国槐。可以说国槐代表了北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没有国槐,胡同里就总觉得缺点什么。
1986年,北京市在评选市树时,国槐与侧柏一起高居榜首。如果说侧柏代表了皇家的庄严大气,那么国槐就代表了北京民居的宽厚包容。
尽管国槐的植物学名称是用日本的“japonica”定名,其实国槐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树种,日本的国槐都是从中国引种的。
张志翔告诉记者,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德国波鸿大学汉学家曾经就国槐在中国的历史与他探讨,并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国槐原产地在中国,后引种到日本,导致后来植物学上的定名采用“日本”名。
我国自古国槐就为公卿大夫之树,《周礼》中有“三公面三槐”的记载。在北京国子监里,古槐成片,其中有一棵双干古槐,据说是元代国子监第一任祭酒许衡所植,距今已700多年,它在明末已枯,但到清朝乾隆年间忽又萌发,被称为“吉祥槐”。
北京国槐种植始于元代。在明清两代,国槐作为北京的行道树大量种植。而近代,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中也多种植国槐。到1980年普查时,北京全市城近郊区共有国槐141796棵。
国槐能成为北京市井主要乡土树种是因为它对北京的土壤气候非常适应,它的根能扎得很深,有很强的吸水肥能力,而且国槐既抗寒又耐高温,对土壤通气性要求也不高,可以在较密实的土壤中生长。
尽管国槐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特性,但随着北京旧城改造,在大量四合院、胡同消失的同时,曾是北京民居文化代表的国槐也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如今,在北京正义路、东交民巷、南池子、南长街等处,还能看到一些作为行道树的国槐,这些多为1935年至1938年种植的。
张志翔告诉记者,除国槐外,过去北京民居庭院中种植较多的还有枣树、香椿树、柿子树等可食果、吃芽的树种。但也随着城市改造拆迁而退出城区,目前在郊区庭院中还多有种植。
更替频繁的行道树种
刘全儒告诉记者,适宜做北京行道树的树种要求耐寒、耐旱、不容易倒伏、寿命长、树形好,而且还不能是果树,因为果树要经常修剪,影响交通,公路边污染也大,果树普遍抗性较差。由于城市绿化的观念改变,北京行道树变化最多。
张志翔介绍,过去郊外生长的树种中榆树较多,尤其在永定河畔有大量榆树自然生长。而且榆树木材坚硬细腻,也是做家具的好材料。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榆树荷兰病开始蔓延,这种病可以传染整片榆树林,造成榆树大面积死亡。
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大量种植杨树作为行道树,主要是华北乡土树种毛白杨和从国外引进的黑杨。张志翔回忆,当时选择杨树作为北京市的行道树与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有关,197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比较选择用于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树种时,发现杨树具有其他树种不具备的适生性,于是北京市也选择杨树作为适生造林树种大面积种植。如今,杨树已经从北方推广到南方,在江西、安徽、湖北等地都有种植。
之后,林业部门又从北美引进了洋白蜡树,天津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津白蜡树,开始在北京替代杨树种植。如今学院路、双清路、北三环路两侧种植的都是津白蜡。
刘全儒告诉记者,以前北京的行道树除杨树外,还有许多柳树,特别是在河堤附近。但是由于早年种植的柳树在生长50年后树心就空了,容易倒伏,再加上杨柳絮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导致柳树与杨树一样都逐渐被其他树种替代。
北京还曾引进过一批泡桐,主要是看中了泡桐生长速度快,能迅速形成绿荫。但是经过几年种植,发现泡桐的树形不好看,而且泡桐容易得丛枝病,常导致幼株死亡,冠形被破坏、生长衰退。所以,泡桐也没有推广开。
张志翔记得,以前在北京三环外菜地与城市隔离带区间种植有大量核桃树,包括清华东路两旁也都有种植,但随着城市发展、道路拓宽,这些核桃树也都消失了。
在2008年奥运会前,为了让北京的绿化环境更加多彩,北京市园林部门开始推广彩叶工程。那时引进了紫叶李、紫叶桃、金枝槐、金枝柳等彩叶树种,沿街道一排排种植,确实给城市街道添了一抹亮色。
被彩叶替代的山区树种
历史上,北京山区的树种以海拔1000米为界,海拔1000米以下多种植侧柏和油松,而海拔1000米以上则以华北落叶松为主。
张志翔介绍,随着新树种的引进,刺槐开始出现在低海拔的北京山区。1910年,德国传教士最先把刺槐从海外引种到青岛,由于刺槐长得快、萌叶强、耐旱好、花蜜产量高,逐渐被引种到北京,主要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阳坡、半阳坡分布。
在2008年奥运会前推广彩叶工程时,山区也是重点。以前,北京山区只有香山地区有彩叶树种,推广彩叶工程后,山区树种开始注重色彩搭配,培育大量黄栌,并把元宝枫与油松混种。
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曲折。因为元宝枫是散生树种,无法形成纯林,在与油松混种后,元宝枫都被压死了,而林下草本植物也都消失,形成碎砾石。所以元宝枫也逐渐被淘汰了。
目前,林业科技部门开始注重栎类树种在北京山区的种植,特别是栓皮栎、蒙古栎。
刘全儒告诉记者,北京退耕还林后,很多山区还种植了果树,比如柿子树、核桃树、板栗树、苹果树、梨树等。张志翔认为,经过多年植树造林,北京已经没有可造林的地方了,因此,绿化的重点应该放在林木保护和人工林改造上。比如对低产人工林,可用其他树种进行替代种植;对纯林,可通过种植其他树种,使其变成混交林。
同时,也提高现有人工林的生态功能,模仿自然森林结构种植树种,比如,在针叶林中发现有数量不多的阔叶树,就要尽力保护,让这些阔叶树能够生长繁茂。
张志翔反复强调,北京绿化应该活起来,不但要有树,还要有鸟,有小动物。这就需要注重绿化层次,有乔木,有灌木,给野生动物栖息创造良好的环境。
刘全儒也认为,北京城市绿化的问题之一是植物配置的结构层次单调,常常形成单一的行道树或单一的绿篱,或单一的草地,虽然在景观上整齐美观,但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所起的作用却较差。因为同等面积的乔灌草复合群落所发挥的生态效益将是单一草坪的4倍。
北京市林业部门十分重视北京市城区的绿化效果,正在积极改变原有的绿化格局,向着体现生态效益、为市民提供近自然的休憩场所努力。
未来,随着植物新品的培育和城市的发展,北京的树种还将继续变迁,北京城市的生态环境必将发挥应有的生态功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直是绿化的目标,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
作者:魏刚
责任编辑:iwcs24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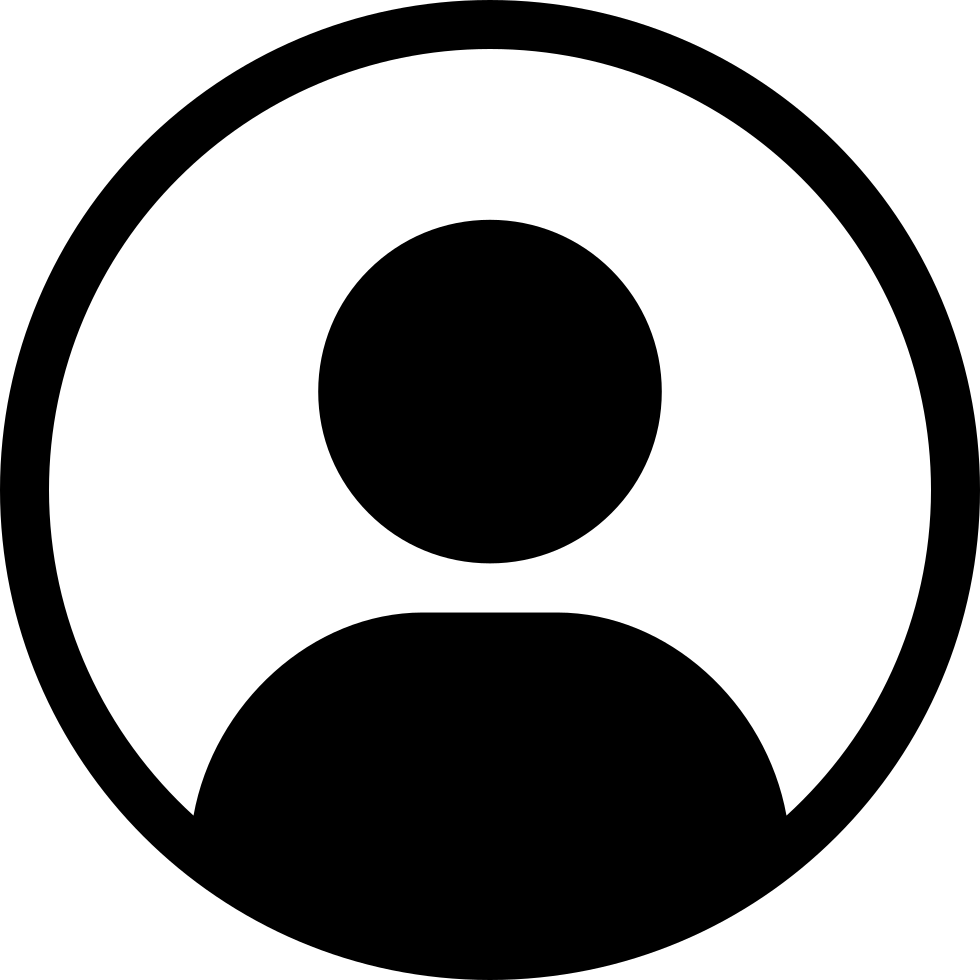
 10,431
10,431